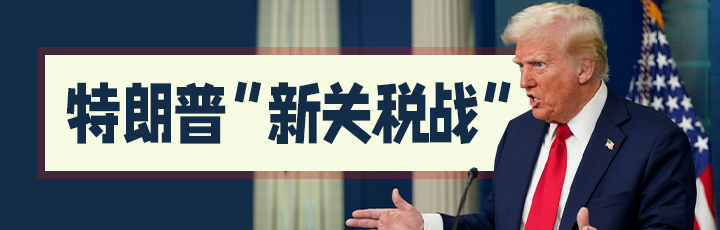在香港,当个人与家庭遭遇困境,市民诉诸社工求助。 然而一河之隔的内地,“社工”之名或被误解为义工或居委会。 此背景下,仍有内地学子负笈而来,最终在港就业安居。 陈烨是“留港社工”的一员,多年来于残疾人士服务、复康服务等领域绽放光芒,更将香港经验带返内地,为当地培训过百名社工。 随大湾区融合,港人北上、“高才”来港打拼的情况增多,她希望担任“文化翻译者”,协助两地社工相互研习,成为彼此的强力后盾,共同改善人民生活。
▲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陈烨盼担任《文化翻译者》,协助两地社工交流学习。
陈烨昔日是一位记者,毅然放下工作,来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工硕士。 她犹记得,离开上海之前,经常到三甲医院采访,目睹来自全国各地的穷苦病患,有人因负担不起床位,睡在门诊大厅的地板上,有人为治病向亲朋好友借积蓄,医药费是用硬币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看着这些病患,她无比心痛,“我告诉自己,希望有天学成归来,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来到香港后,她从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苦练成为能与本地人沟通。 毕业后她先后在不同社福机构工作,为青少年及残疾人士提供服务,亦曾于家长自助组织,为家长发声及作出支持,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工之路。 特别的是,在香港工作4年多,她同时在顺德担任社工督导,开始每月在粤港两地奔波,将在港任社工的经验,分享给内地社工,直至疫情才中止。
将理论作系统性整合让学生跟上
陈烨说,对比香港有完善的训练、实习和注册制度,“内地社工专业起步较迟,不一定接受过专业训练,对社工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有限。”她指,内地的服务模式不同,如她曾到访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不少社工非社工系出身,亦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当地社工薪酬较低,我需要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处境,不会以香港这一套去衡量他们。”
她将社工的理论作系统性整合,为让没有相关基础的社工学生跟上,花了大量时间备课,加入实际例子,并作互动教学,“我备课时间是1比1,甚至1.5比1,因为我真的想他们有更好的学习成果。”不仅上课,她更为学生做示范,亲自拜访学生的个案,在取得对方同意下,现场展示辅导过程和技巧。 为不耽误香港的工作,她有时会选择即日往返粤港,头班车去、末班车回,仅乘车便要6小时,回家后已累得没有任何力气。
由于两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当中衍生服务模式的差异,内地学生学习起来有点困难,进展缓慢,一度让陈烨感到担忧。 她形容,那种感觉像将水倒在沙漠上,“不论倒多少,都好像挥发了,令我也有点沮丧。”后来,她却发现原来并非沙漠,只是一片干旱的土壤,储存的水足够多,种子仍可开花结果。
她分享,有次看见学生运用“空椅子”理论处理家长的哀伤期,于是作出称赞,并询问对方如何做到,“学生说,其实我上课时大家都有认真听,只是当时未消化到,需要一些时间理解,之后便尝试去用了。”
个案与本身文化社会背景有关
陈烨说,在内地做社工,会看到有中国特色的个案,“原来社会工作,真的与本身文化和社会背景有关。”她举例,有因拆迁突然富裕的地区,背后衍生许多家庭问题,如“包二奶”、赌博、吸毒。
另外如在农村,妇女较不被容许表达情绪,她提到,当地社工接获其中一个案,妇女在煮饭时,其5岁儿子不幸从2楼坠地身亡。 妇女面对家族指责,加上自身罪恶感,惟不能表达个人情绪,于是外化为指责村委。 当地社工不知如何处理,她提醒重点不在拆解村委与妇女之间的纠纷,而是令众人理解事件为意外,以及引导家人支持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走过眼前难关。
陈烨的耐心和同理心,为内地社工团队带来启发。 不少学生开始主动与她探讨具体的辅导方法和临床技巧,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水平,也增强对社工工作的认同感。 她笑说,“我看见他们的转变,也很有成功感。”她的第一批学生后来也成为当地机构的管理层,她说,“内地有宏大的社工需求,我的帮忙像一滴水倒入大海,但我相信每人的一滴水,也可让努力被看见。”
两地系统互补能省处理文件时间
疫后通关,两地的交流互动增多。 陈烨说,近一年很多香港的服务机构主动联络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讨论举办交流团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的角色正好是两地的文化翻译者,希望能为香港和内地的社工界,搭建交流的平台。”
她说,香港自有内地可以学习的社工系统,而内地采用大数据的信息化系统,能减省社工处理文件的时间,可以互相弥补。
近年不少港人北上求助、养老,亦有大量内地优才、高才来港,两地的融合亦让社工模式迎来新挑战。 陈烨说,有跨境院舍便希望通过协会联络留港社工,期望让他们在内地工作的同时,也可受聘于香港机构。
至于优才、高才,陈烨说,有关人才的需求与过去的内地新移民不同,大多是受教育人士,离乡别井下获得的支持更少,“我们很乐意以来港的身份和他们接触,亦相信我们可以发挥的角色会越来越多。”
她形容,自己“踩在两条船上”,而两河之间正好有缺口,作为留港社工,希望为两地社工界作出回馈,“将社工的价值传递出去,社会上多了一些美好的人性,就是有意义的事。”
采访南亚海啸陷压力症 激发做社工实际助人
陈烨早年从事传媒,2004年的南亚海啸是其人生的转折点。 她当时在上海一间报社任记者,被紧急调派往泰国采访灾区重建情况,当中经历让她更渴望帮助受苦的人们,毅然辞职来港读社工。
▲陈烨昔日从事传媒工作。
那年是陈烨当医疗卫生和科技线记者的第二年,被派往泰国布吉采访灾后现场,亲眼目睹灾民的种种困境,其内心深受震撼。 完成采访后,她前往尸体焚化处报名做志愿者,被拒绝之际,一位泰国华裔心理学系研究生向她主动搭话,在其帮助下,得以顺利把上海医疗队留给她的药物发放给灾民。
她发现,灾民与男学生很熟络,全心全意依赖他,“那位男生说,灾民需要的不光是物质救助,更需要心理救助。”男孩的一句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返回上海后,陈烨陷入创伤后压力症的困扰,总闻到尸臭味,看到海浪就忍不住落泪,久久无法释怀。 在反复思考和挣扎中,她希望做能实际助人的工作,想起昔日采访时对心理咨询有兴趣,最终下定决心,放弃既有工作,只身来港入读社工系,毕业后留港工作至今。
以佛教智慧应对工作挑战 不执着沉溺负面情绪
陈烨坦言,社工工作压力甚大,每项决策都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的未来,故保持早睡早起尤为重要,以维持良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求助者有成长,可以带给我动力,但无可否认,亦有很多个案较复杂,令人心情沉重。 对我而言,信仰是很大的支持。”
▲陈烨在港受邀分享内地督导的心得与体会。
她形容,辅导者像一个容器,“清空得越快,可承载的事物便越多。”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她认为佛学思想有助其保持清醒和冷静,“佛教强调每人有因果业力,有各自的命运,让我不会过于执着,沉溺在负面情绪当中。”
此外,她说,佛教内的修行,如颂经、冥想等,也能使她清空脑海的杂念,保持内心平静,“避免受个人主见所局限,以更开放、包容的心对待求助个案。”
以上内容归星岛新闻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