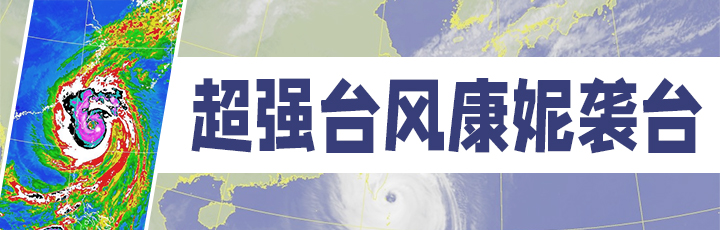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程 实

图:减税优惠带动,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指数上升。
美国通胀超过3%的支出类别比例,从2020年1月的23%上行至2022年1月的69%,欧元区的比例从9%上行至39%,高通胀影响范围正在逐步变宽。中长期来看,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高通胀会否延续且进入自我强化的第二阶段?答案取决于“薪资─价格”螺旋。
基于数据分析和学术研究,笔者提出了判断“薪资─价格”螺旋出现的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积极财政导致家庭部门储蓄过剩,劳动参与意愿降低;二是私人部门定价能力抬升,企业薪资抬升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三是工人议价能力抬升,薪资外溢效应通过公共部门开始扩大。
其中,积极财政是“薪资─价格”螺旋出现的基础,私人部门薪资抬升是“薪资─价格”螺旋的核心驱动力,而公共部门和工会组织引发的薪资外溢效应则对“薪资─价格”螺旋起到一定助推作用。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在有限的数据中,笔者认为欧美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陷入“薪资─价格”螺旋之中,尽管部分发达国家长期通胀预期已经出现见顶下行的迹象,但各国央行仍需要高度关注“薪资─价格”螺旋的外溢效应可能带来的再通胀(第二轮通胀)风险。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同样需要根据通胀预期变化积极恢复疫情前的制度结构,毕竟现行的制度结构将加剧“薪资─价格”螺旋上升。
条件一:家庭部门储蓄过剩、劳动参与意愿降低
根据研究发现,疫情前后欧美名义可支配收入大幅上涨。具体来看,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PC)的最新数据显示,发现疫情期间《美国救济计划》帮助美国家庭的税后收入提高了4%,而有孩子的家庭平均减税额度为6000多美元。从社会阶层看,中低收入家庭(年收入9.1万美元或以下的家庭)从参议院的救济措施中获得近70%的税收优惠;在有孩子的中低收入家庭中,2021年的减税优惠高达75%。这导致了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指数,从2019年第四季的100增长至2022年第一季的112。
欧元区的情况类似,通过积极财政补贴帮助雇主(企业)支付工资,使得员工劳动力收入在疫情期间得到稳定保证,而无薪休假计划帮助更多的劳动人口保留了劳动岗位。欧元区家庭可支配收入指数,从2019年第四季的100增长至2021年第四季的103。
财政政策不仅保护了家庭收入,更帮助欧美积累了被压抑的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期欧美房地产市场及家庭消费最终支出能够表现强劲。同时,尽管受到地缘和疫情冲击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但欧美家庭部门对高通胀的容忍度显著提升了,这是因为欧美财政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欧美家庭部门积累了大量非自愿的过剩储蓄,额外的财政收入弥补了家庭部门的通胀损失。此外,过剩储蓄导致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后期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降低,可以说积极财政是“薪资─价格”螺旋产生的基础条件。
条件二:企业定价能力与雇员议价能力同步抬升
当能源价格或居民部门对通胀的容忍度提高时,如果市场总需求保持强劲,企业在定价时,会更多考虑价格因素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如果企业认为竞争对手提高价格的概率较大,那么该企业通常会选择将成本转移给最终消费者。企业薪资提高的外溢效应,会刺激通涨价格的传导开始变宽(从上游向下游影响),并且伴随着可能产生的反馈效应,最终导致“薪资─价格”螺旋增长。
当前,欧美企业定价能力及工人(或雇员)的议价能力正在同步抬升。这是因为疫情后欧美市场的被抑制需求(Pent-up demand)大幅反弹,企业因此能够容忍劳动供给紧缺带来的薪资水平上涨。
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会担心利润率下滑,而是会通过调高价格来提升整体销售额。通过用价格相对于成本的加价衡量企业定价权,笔者发现当前美国企业的定价权已经处于过去40年的高位,在外生冲击环境下,企业通过财政及货币政策的补贴或信贷支持,将总价格的变动纳入定价决策,导致企业定价权力提高,这将加剧薪资和价格之间的反馈。
从行业角度来看,当前零售类企业和酒店餐饮类企业的薪资增长较为强劲。以美国为例,近期美国零售、餐饮、酒店及航空等行业的薪资增长,正在加剧一般服务类行业的价格黏性。由于疫情和地缘风险对这些敏感行业的显著影响,使得这些相关行业的劳动市场需求缺口持续扩大,最终造成通胀压力逐渐渗入到CPI篮子的各个项目中,尤其是那些更具黏性的服务业项目。但从历史数据来看,酒店餐饮与零售类企业的薪资调整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对其他行业薪资的外溢效应影响有限。
笔者认为真正需要高度关注的是,近期制造业企业薪资水平持续上涨可能引起的外溢风险,制造业薪资上涨能够通过全球供应链快速放大对可贸易部门薪资水平的溢出效应。总体来说,企业或私人部门定价权力抬升,本质上是市场供需失衡导致的,一方面总供给偏紧使得企业被迫抬升薪资水平;另一方面,总需求强劲使得企业有了更大的空间,将总成本转移给下游消费端。因此,“薪资─价格”螺旋的形成与持续性,根本是由市场供需的失衡程度所决定。
条件三:薪资溢出效应通过公共部门扩大
当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供给小于需求)时,工人议价能力变强,而议价能力提升带来了名义薪资增长。此时,工薪阶层会要求补偿近期购买力的损失,通过确保获得额外收益来弥补通胀溢价抬升带来的潜在风险。
从制度层面来看,当外生冲击破坏了原有僱佣关系和工作模式时,新的劳动供需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劳工组织和协议的重置成本会因为工人议价能力的提高而上升。尤其是受疫情或地缘影响显著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涉及了大量工人群体的薪资协议重置,将对整个行业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这是由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线,可能会扩散影响到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其他行业的相关工会组织因此会有理由向企业施压,并通过谈判提高最低薪资水平和相关福利待遇,导致薪资溢出效应通过公共部门开始扩大。
比如,在2021年底发生罢工后,美国大型企业已经同意在薪资合同之中加入COLA条款(Cost-of-living Adjustment,生活成本调整),这导致美国社保金COLA大幅上升,相比2020年1.3%的水平,2021年美国社保局将年度生活成本调整(COLA)为5.9%。也就是说从2021年1月开始,个人平均退休福利将提高至每月约92美元。而进入2022年,COLA进一步上调至7.4%,这是自1983年1月以来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最大增幅。类似的情况,近期英国工会组织与企业达成了10%的加薪协议。在法国,巴黎工会也已经要求将最低薪资提高至25%。
此外,2022年德国也同意大幅提高最低薪资水平。尽管当前公共部门对最低薪资水平调整,对其他行业或部门薪资的溢出效应可能会比低通胀时期更大,但是如果从过去40年来看,最低薪资增长对其他薪资的溢出效应仍然有限。实证来看,公共部门薪资的增长相比企业部门薪资增长更难导致系统性的溢出效应,这是因为最低工资水平对社会平均薪资水平的影响正在减弱。因此,公共部门薪资提高的溢出效应对“薪资─价格”螺旋主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来源:大公报